青春励志小说《难产时丈夫选择保小,他悔疯了》是一部言情题材的佳作,作者青梧和光通过主角程砚张佩兰陆心念的成长历程勾勒出了一个鲜活的形象。小说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激励读者拼搏奋斗,传递着积极的能量和正能量。越来越多的鲜血从身下流出。浓重的铁锈味几乎要将我淹没。就在我意识即将消失时,我听到几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有医生紧绷到沙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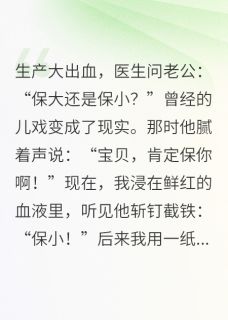
《难产时丈夫选择保小,他悔疯了》免费试读 难产时丈夫选择保小,他悔疯了精选章节
生产大出血,医生问老公:“保大还是保小?”曾经的儿戏变成了现实。
那时他腻着声说:“宝贝,肯定保你啊!”现在,我浸在鲜红的血液里,
听见他斩钉截铁:“保小!”后来我用一纸死亡证明结束了这场婚姻。五年后巴黎珠宝展上,
程砚拿着钻戒当众下跪求我。“念念,回来吧。”我晃了晃无名指的婚戒轻笑。“程总忘了?
当年签字保小的那一刻,我就死了。”1我紧紧攥着拳头,指甲几乎掐进掌心。每一次呼吸,
每一次用力,都伴随着无尽的折磨与痛苦。我感觉身体在逐渐的失温,
越来越多的鲜血从身下流出。浓重的铁锈味几乎要将我淹没。就在我意识即将消失时,
我听到几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有医生紧绷到沙哑的询问。“保大还是保小?”恍惚地,
我想起多年前我与程砚刚刚结婚时。
我窝在柔软的沙发上看着电视里上演烂俗的生死抉择桥段,故意坏心地揪着程砚的耳朵问。
“要是我也这样,保大还是保小啊?”那时他放下平板,低头在我颈边蹭着,
温热的气息扑在我敏感的皮肤上,引起一阵痒意和微麻的电流。“别问傻问题,宝贝儿。
”他腻着声,故意在我耳边厮磨,气息滚烫。“老公命给你都行,当然保你啊!
”“我只要我的宝贝!”医生催促的询问声再次响起,将曾经泡沫般的幻影一下子击碎。
世界仿佛突然安静了下来。片刻后,我听到了程砚那无比熟悉的声音。
可内容却带着斩钉截铁般的冷漠。“保小。”短短的两个字。干净利落,
没有一丁点拖泥带水,甚至没有一丝多余的波澜。
他仿佛只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这样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心底那座名为“爱”的高楼,
被他这犹如冰锥般的两个字彻底击垮。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死死糊住了我的双眼。
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哆嗦,失血的寒意从四肢末端蔓延。冰冷刺骨。可这寒意,
不及心口的万分之一。意识沉入无边黑暗前,手术仪器的尖锐鸣叫仿佛成了背景。
唯有那两个字,如索命咒语,在深渊里无尽回响。保小。
保小......2意识还漂浮在黑暗中。
身体已经提前一步感受到了难以忍受的酸痛与麻木。费力地,
几乎是调动了全身仅存的那点气力,我终于颤抖着掀开了一点眼皮。
眼睛立刻被刺眼的白光**得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水雾。“醒了!病人醒了!
”一个年轻的、带着几分惊喜的女声在喊,随即是更密集的脚步声凑近。嗓子又干又疼,
嘴唇也无比干裂。就在这时,一只带着医用手套的手用一根沾着水的棉签,
小心翼翼地润湿了我的嘴唇。我虚弱地笑了笑。
随即视线被对面放在无菌箱里小小的婴儿整个夺走。他皮肤红红的皱皱的,眼睛紧闭着,
只有小小的胸膛在微弱地一起一伏。
那么弱小、那么脆弱......是我废了半条命才生下的孩子。
......更是他在二选一中义无反顾的抉择。我沉默地看着孩子,心中没有半点欣喜,
反而被浓重的绝望与悲伤牢牢笼罩着。让我几乎喘不过气。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
保姆王姨那张永远挂着讨好的笑的脸庞探了进来。“哎哟喂,我的小祖宗,可算安生了!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却也抑制不住的欢喜,
直直地对着站在保温箱旁边的程母张佩兰小声嘀咕。“瞧瞧这眉眼,
跟砚哥儿小时候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鼻子,一看就是程家的种,福气大着呢!
”张佩兰显然是一副精心打扮过的样子。她看着沉睡中婴儿的目光,
透露着一股打量与高高在上的矜持感。像是在评估物件一样。
“老太太盼了这么久的曾孙子可算是盼下来了,这下好了,四代同堂,
家里那个镇宅的老佛爷总算能安心了。”她说着,嘴角微微向上扯了一下,转瞬即逝。
“说起来,孩子妈命也是硬,这么折腾居然也撑过来了。就是可惜......”终于,
她总算是想起来了病房里躺着的另一个人。随后目光吝啬地、极其冷淡地朝病房里扫了一眼,
像是在评估一件损坏了的工具。“这身子骨,怕是大伤元气了,
再要下一胎可......”一股突如其来的恶心与眩晕感将我整个淹没。命硬?可惜?
下一胎?我感到强烈的荒谬与可笑。原来如此。我在他们眼中,不过是生育工具。
现在这个工具“零件磨损了”,没有价值了下一步,她们是不是毫不在意要将我一脚踢开?
然后接着去找另一个让他们所称心的工具?我的胸口一阵刺痛,忍不住发出一声痛苦的呜咽。
门口的张佩兰和王姨同时扭头看过来。张佩兰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眼中掠过一丝被打扰的厌烦。“睡醒了?”张佩兰语调平平地问。王姨倒是反应快些,
脸上的笑容瞬间调整回那种“专业”的、带着距离感的关怀姿态。她快步走到床边,
声音刻意放得柔顺。“太太您醒啦?可吓死我们了!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吃点什么?
”她的目光却带着某种灼人的审视,飞快地从我毫无血色的脸扫到盖在被子下的腹部。
眼神中明晃晃地在评估盘算着我的身体是否还有“再利用价值”。
王姨那张虚假堆笑的脸恶心地令人窒息。我疲惫地把头扭到一边。
任由眼角的泪水不争气地浸湿床单。3出院的日子,空气也灰蒙蒙的。身上的痛楚稍稍缓解,
心口的空洞却越来越大了。门被推开。是程砚。他逆着光站在门口,
眉宇间带着一丝工作后的疲惫。他看着我,深邃眼眸复杂难辨。有疲倦,有不耐,
似乎还有一抹一闪而过愧疚?“好点了吗?”程砚走过来,停在床边几步之外,不再靠近。
我眼睫低垂着沉默。没有理他。他站了片刻。我的沉默显然挑战了他岌岌可危的耐心。
他紧皱着眉,忽然弯腰靠近。带着烟味和压迫感的气息向我逼近。一瞬间,
大出血那日的痛苦死死将我笼罩。那句“保小”如同雷鸣般再次在我耳边回响。
强烈的排斥感让我身体瞬间绷紧,躲过了他的触碰。程砚捕捉到我的抗拒,眼神倏地一冷。
“陆心念!”他声音带着被拒绝的不耐。下一秒。他竟猛地抬手,
冰冷的手指狠狠攫住我的下巴,强迫我抬头直视他!我脸上闪过吃痛的神色。
可程砚丝毫不在意我的感受,他冲我低吼着,向我发泄着心中的不满与不耐。“说话!
摆这副样子给谁看?!”我沉默地与他对视。从他的眼中,
我看到了自己疲惫、苍白又心如死灰般的面孔。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好几十岁。
而程砚在短暂的愤怒后,眼睛中闪过一丝慌乱与后悔。我好笑地扯了扯嘴角。
他竟然还会后悔吗?“那日我听见了。”我直直地看着他,强作平静道。“你说保小。
”话音刚落。程砚的身体,极其轻微地震颤了一下。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
瞬间掀起惊涛骇浪。愤怒?无措?慌乱?各种情绪在他眼底激烈碰撞,快得让人抓不住。
那瞬间的慌愣,像投入冰湖的石子,激起一圈微澜。但也仅此而已。很快,
那点涟漪被更加坚硬冰冷的愠怒取代。他甚至没有松开钳制我下巴的手。“所以呢?
”程砚声音更沉,带着一丝压抑的烦躁和莫名的刻薄。“你现在不是还没死吗?!”没死?
原来在他眼里,只要没死,那份用生命去“选择”的背叛,
那份在手术台上被恐惧和绝望撕碎的痛楚,就可以轻飘飘地揭过?我的心脏狠狠揪成一团。
巨大的荒谬和无力死死将我包围。许久,我长长地叹了口气,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哑声道。
“......我们离婚吧。”室内瞬间死寂。程砚的脸色瞬间黑成一片。他死死盯着我,
那眼神凶狠得像是在看仇人一样。“呵。”一声充满嘲讽的冷哼从他喉间溢出,他咬牙问我。
“陆心念,你闹够了没有?!”他猛地直起身,居高临下,周身散发着骇人的低气压。
“生个孩子,矫情成这样?我选孩子怎么了?那是我的亲生骨肉!”他烦躁地扯了扯领带。
“我看你是疯了。你自己在这里冷静冷静!”话音落下,他毫不犹豫地转身。
“砰”地一声巨响,他用力地摔门而去!病房重归死寂。我缓缓侧过头,
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泪水悄无声息地从眼角滑落。4我被强行接回了程家那个牢笼。
沉重的铁艺大门滑开,露出王姨那张堆满假笑的脸。“太太可算回来啦!
”她热切伸手过来想要搀扶我。我厌恶地躲开她的触碰。王姨的动作顿时僵住。
张佩兰站在台阶上,高高在上,冰冷地审视我。“行了,到家了,杵着干什么?王姨,
扶她进去。”我拂开王姨再次伸来的手,一步一挪,独自走进这个如同深渊般的囚笼。
程砚借口工作忙,一直拒绝和我交流。我成了这巨大宅邸里一个透明、碍眼的废品。
王姨“伺候”得愈发敷衍。水是凉的。饭菜要么寡淡无味,要么油腻难咽。这天傍晚,
王姨端着一碗寡淡的青菜粥进来,小声抱怨。“老太太吩咐的,说太太刚生产完不久,
虚不受补,清粥养人......”清粥?我抬起眼。碗边凝着一层厚厚的油光。
里面的粥早已变得冰凉。呵,这就是所谓的养人吗?张佩兰正好进来“看看”她的大孙子。
她瞥了一眼碗,嘴角微撇。“怎么了?不合胃口?”她的语气带着长辈特有的、虚伪的关心。
“程家几代单传的独苗,可不能饿着他妈。”我的心被她这番不阴不阳的话狠狠剜了一下。
程砚刚好推门进来。他刚从公司回来,身上带着寒气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他看到了桌上的冷粥,目光在我虚弱的脸上停留了一瞬。
我心中竟荒谬地闪过一丝微弱到极致的期望。他会说什么?可程砚径直走向婴儿照片墙,
看着儿子最新拍的照片,眉宇间是清晰的柔软。他甚至抬手轻轻触摸了一下照片上的笑脸。
然后,他仿佛才想起屋里还有一个人。他走过来,站在桌边拿起瓷勺,
舀了一小口冷粥送入口中。喉结微动,随即咽了下去。“凉了,但能吃。”程砚放下勺子,
只是简单地嘱咐句。“王姨,下次让厨房注意点温度。”整个过程他的目光甚至没有看过我。
没有维护,没有怒斥,连一句“换掉”都不屑于说。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能吃”。原来,
在他和他家人的眼里,我就配吃这样的东西。因为我是“生不了二胎的废物”,
连一份热饭都成了奢望。我好笑地扯了扯嘴角,无视那碗凉粥,沉默地离开房间。
张佩兰眼底掠过一丝满意,继续欣赏着墙上的孙子照片。程砚似乎还想说什么。
可“砰”地一声。我猛地关上门。与他们划清了界限。5如此虚与委蛇了几天。
我静静地坐在窗边,听着客厅中程家人的欢声笑语。程老夫人难得高兴,她兴致勃勃地提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