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候假爷爷四年,他全家傻眼了》是一部扣人心弦的言情小说,由裴圭里倾力创作。故事以傅砚川宋知意林晚为中心展开,揭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随着剧情的推进,傅砚川宋知意林晚不断面临挑战和考验,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内心的真正力量。这部令人惊叹的与此同时,沪市的别墅里。傅砚川在天亮时,才小心翼翼地从宋知意的温柔乡里起身。不知道为什么,他右眼皮一直在跳,心里莫名有些……将让你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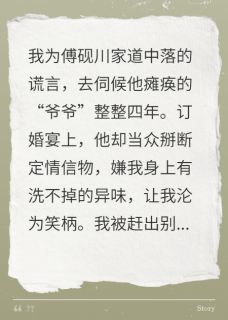
《伺候假爷爷四年,他全家傻眼了》免费试读 伺候假爷爷四年,他全家傻眼了精选章节
我为傅砚川家道中落的谎言,去伺候他瘫痪的“爷爷”整整四年。订婚宴上,
他却当众掰断定情信物,嫌我身上有洗不掉的异味,让我沦为笑柄。我被赶出别墅时,
才听到真相。原来一切都是他和白月光的赌局,用我的十年作践我。他们以为我走投无路,
会回去摇尾乞怜。可他们不知道,那个被我照顾的老人,是他们杀人案的唯一证人。
他们全家都慌了。1订婚宴上,傅砚川亲手掰断了我手腕上那只血玉镯子。清脆的断裂声,
像根针,扎破了满堂的喜气。那只镯子,是他母亲传给他的,傅家最值钱的家当。四年前,
傅家生意崩盘,他说哪怕把房子卖了,也要把这只镯子留给我,这是他对我的承诺。而现在,
他攥着那半截断玉,像是捏着什么脏东西,眼神比看垃圾还要冷。「各位,抱歉。」
他的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宴会厅鸦雀无声,「我和林晚的婚事,就此作罢。」他母亲,
准婆婆秦岚猛地站起来,脸色铁青:「砚川,你疯了!?」傅砚川没理她,径直走到我面前。
他俯下身,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听到的音量,吐出最淬毒的话:「林晚,
你知道吗?我每次抱你,都能闻到一股味儿。那股……伺候瘫痪老头四年,
怎么都洗不掉的尿骚味儿。」我的大脑“嗡”的一声,炸开了。他猛地直起身,
把我拽了起来,撸起我的袖子。
袖遮挡的手腕和小臂就这么暴露在刺眼的灯光下——因为长期用力搬扶一个三百多斤的男人,
我的腕骨微微变形,皮膚下面是常年不散的青紫色瘀痕。「我傅砚川,」他扬声,
对着所有宾客,「绝不会娶一个这样的女人进门。」他没说我做过什么,
但那欲言又止的态度,配上我手腕上骇人的痕迹,给了所有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宾客们窃窃私语,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探究。「看看她那手腕,天呐,真吓人。」
「听说她跟了傅砚川快十年了,从大学就跟着,不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活儿吧?」
秦岚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快步冲过来,一杯红酒劈头盖脸地泼在我刚化好的新娘妆上。
「**!你到底背着我儿子做了什么勾当!」她尖叫着,扬手就想打我。傅砚川退后一步,
完美地避开了这场闹剧的中心。他眼睜睜看着我被他母亲推倒在地,
看着那些混着酒精的唾沫星子喷在我脸上,
看着他那些亲戚像围观什么脏东西一样对我指指点点。他转身就走。背影决绝得,
好像我们十年来的所有情分,都只是一个笑话。我穿着那身量身定制的白色礼服,
趴在冰冷的地板上,浑身狼藉。手腕上那半截断掉的玉镯,锋利的边缘死死硌着我的皮肤。
又冷,又疼。2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逃回别墅的。推开门,客厅里一片黑暗,
只有书房的门缝里透出一点光亮。我浑身湿透,红酒渍和泪水混在一起,黏在皮肤上,
又冷又痒。书房里传来傅砚川和他表弟秦凯的说话声。「哥,你真就这么跟嫂子……不是,
跟林晚分了?在订婚宴上那么羞辱她,是不是太狠了点?
她那四年……可是真的把命都搭进去伺候你爷爷了。」我捂住胸口,脚步像是被钉在了原地。
然后,我听见傅砚川的一声嗤笑,轻飘飘的,像在掸掉烟灰。「命?一条贱命罢了。」
「你当初又不是不知道,那老头子根本不是我亲爷爷,就是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
半身不遂,脾气又臭,家里谁愿意伺...候?也就林晚那个蠢货,
我编个家道中落、全家为医药费愁白了头的故事,她就信了。」「我当初跟她说,
家里破产了,就剩那只血玉镯子。只要她愿意替我去尽这份‘孝’,等爷爷走了,
家产就有她一半。你看她当时那样子,眼睛都亮了,哭着喊着说愿意。
以为自己是多伟大的情圣,其实不过是个被‘未来遗产’冲昏了头的捞女。」
秦凯似乎有些不忍:「可她毕竟坚持了四年……吃喝拉撒,比亲孙女还亲。她手上那些伤…」
「停。」傅砚川的声音冷了下来,「别提了,恶心。」「本来,我也不是不能给她这个名分,
就当养条狗了。可你知道吗?知意昨天给我发消息了,她要回来了!她后天就到!
她问我这几年有没有乱搞,知意有感情洁癖,你懂吗?
我绝不能让她知道我和一个伺候瘫痪老头四年、身上带着异味的女人有过什么!
否则她又要生我的气了。」「为了知意,只能委屈一下林晚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闹不出什么花样的。」「你放心,我查过了,她这几年被我哄着跟以前所有朋友都断了联系。
她现在除了我,谁都没有。不出三天,她自己就会乖乖回来求我。到时候,
我找个远点的房子把她养着,也算对得起她那四年‘辛劳’了。」门外的我,
浑身的血液像是瞬间被抽干,又被灌入了冰冷的铅。原来,家道中落是假的。
相濡以沫是假的。就连他口中那个让他夜夜难安的“爷爷”,
也是用来测试我、利用我、作践我的一颗棋子。那什么是真的?我抬起手臂,
看着那些扭曲的筋络和丑陋的瘀痕,那些日夜不停地给老人翻身、**、擦洗身体留下的,
无法磨灭的痕迹……是真的。那些半夜被老人的**惊醒,
一边哭一边给他接屎端尿的夜晚……是真的。巨大的恶心和背叛感从胃里翻涌上来,
我眼前一黑,几乎窒息。书房里的声音还在继续。「那……知意姐那边,哥你打算怎么说?」
我撑着墙,没再听下去,拖着灌了铅的双腿,跌跌撞撞地上了楼。
我曾以为我手里握住的是爱情。现在才知道,那是一把**我自己骨头里的刀。
3我在浴室里冲了整整两个小时。热水开到最大,皮肤被烫得通红,可我总觉得,
傅砚川说的那股“味儿”,像跗骨之蛆,刻进了我的每一寸骨肉里。当我裹着浴袍出来时,
傅砚川正站在卧室中央,秦凯已经走了。他看着我惨白的脸,皱了皱眉,
似乎还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怜悯。「为今天的事生气?」他走过来,习惯性地想搂我的腰,
被我侧身躲开。他的手僵在半空,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林晚,你以前不这样的。
你应该懂事,知道我这么做一定有我的苦衷,而不是在这里给我甩脸色。」又是这种话。
十年了,每当我稍有不满,他就会用这句“你应该懂事”来堵住我所有的话。我看着他,
忽然觉得无比可笑和陌生。就在这时,别墅的大门被人从外面用钥匙打开了。
一道明艳的身影踩着高跟鞋走了进来,她看到傅砚...川,立刻扔掉手里的行李箱,
像只花蝴蝶一样飞奔过来,直接跳到了他身上。「砚川!我想死你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傅砚川的脸上瞬间绽放出我从未见过的狂喜,他熟练地双手托住女人的臀部,
将她稳稳抱在怀里。「知意!不是说明天才到吗?怎么提前了?」「想给你个惊喜嘛!」
宋知意在他脸上用力亲了一口,然后像炫耀战利品一样,目光落在我身上,「我听说,
你这些年为了等我,可是干净得很。我很高兴。」她的视线在我湿漉漉的头发和浴袍上扫过,
嘴角勾起一抹毫不掩饰的轻蔑。「你就是林晚?
那个……帮砚川照顾了他家远房老亲戚四年的……‘好心人’?」我的心脏像是被人攥住了,
喘不过气。宋知意从傅砚川身上滑下来,一步步走到我面前,个子不高,压迫感却极强。啪!
一个耳光,清脆响亮。我被打得偏过头去,脸上迅速浮起五道指印。「伯父伯母都跟我说了。
」她欣赏着我的狼狈,笑了,「你做得那些‘好事’。」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录音笔,
按下了播放键。一阵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女人哭声传了出来,夹杂着粗重的喘息,
和低低的祈求。「求求您,就吃一口吧……就一口……」
「别动了……我给您换……求您了……」是我……是我在某个深夜,
被那个半身不遂的老头折腾到崩溃时,边哭边哄他吃药的录音。是我最绝望、最卑微的时刻。
录音笔里,我的哭声断断续续地回荡着。而客厅里,宋知意贴在傅砚川的怀里,
笑得花枝乱颤。「林晚,你说你好端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
怎么就非得去干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儿呢?」我茫然地看着她,又看向傅砚川,
他自始至终没有看我一眼。「你是不是忘了?」宋知意凑到我耳边,「出国前,
是我跟砚川打的赌啊。我说,像你这种自命清高的女人,骨子里最贱了。
只要给他一个足够悲惨的剧本,你就能把自己作践到泥里去。现在看来,还是我了解你。」
我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哦对了,」她忽然想起了什么,笑得更开心了,
「你知道砚川当初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吗?因为我们俩玩真心话大冒险,我输了。
我的惩罚就是……让当时追我最紧的傅砚川,去追我们班最不起眼的丑小鸭。」「林晚,你,
就是那个最大的笑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锥子,扎进我的心口。原来从一开始,
从十年前那个下雪的夜晚,他捧着热奶茶对我告白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
就只是他们的一场游戏。4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猛地挣脱了傅砚川下意识的钳制,
一巴掌狠狠地甩在宋知意脸上。宋知意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随即眼眶一红,
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柔弱地缩进了傅砚川的怀里。
「砚川……你看她……她把我们俩的过去,
都怪在我身上……早知道……我就不该回来给你这个惊喜……」「怎么敢的啊你!」
傅砚川的怒吼几乎要掀翻屋顶。他眼里的心疼像是要溢出来,抱着宋知意,
另一只手抓着我的头发,把我狠狠地往后一扯,迫使我仰起头。「给知意道歉。」
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凭什么?」我看着他,眼泪终于决堤,「傅砚川,
你玩了我十年,把我当狗一样耍了十年,现在还要我跟她道歉?」「看来不给你点教训,
你不知道自己算个什么东西!」他拖着我,像拖着一条破麻袋,穿过客厅,打开别墅的大门,
然后一把将我推了出去。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倾盆大雨,
冰冷的雨水瞬间浇透了我单薄的浴袍。「你不是想知道我给她什么惊喜吗?那我就告诉你。」
宋知意的声音从门内传来,带着胜利者的娇嗲,「我把自己空运回来,奖励给他啊。」
「滚出去!」傅砚川对着我吼道,「你什么时候想明白自己错哪儿了,
什么时候再想进这个门!」别墅的厚重木门在我面前“砰”的一声关上了。几秒后,
我听见了宋知意一声短促的惊呼,紧接着便是傅砚川压抑的、急切的喘息声,
和衣物被撕开的声音。隔着一扇门,里面是他们的天雷地火,外面是我一个人的地狱。
这场长达十年的骗局,终于在我被当成祭品,献祭给他和他白月光重逢的这一刻,
落下了帷幕。雨越下越大,我被冻得浑身发抖,仅存的那点尊严,也随之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我没带任何东西,手机、钱包,所有的一切,都留在了那个已经不属于我的房子里。最终,
我在齐膝深的积水里,晕了过去。5再醒来时,我躺在一间温暖干燥的病房里。
手背上打着点滴,额头和脸上被划破的地方都贴上了纱布。一个穿着黑色西装,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站在床边,见我醒来,微微躬身。「林**,您醒了。放心,
这里是琼州,我们已经离开沪市了。」琼州……我安心地闭上眼,昏沉沉地又睡了过去。
与此同时,沪市的别墅里。傅砚川在天亮时,才小心翼翼地从宋知意的温柔乡里起身。
不知道为什么,他右眼皮一直在跳,心里莫名有些发慌。他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是派去看守我在另一处房产的保镖。「她人呢?什么时候过去的?」
电话那头的人一片茫然:「傅先生?林**已经搬过来了吗?我们没见到人啊。」
傅砚川夹着烟的手,抖了一下。6我在琼州的海边疗养院待了整整半个月。半个月里,
没有任何人来打扰我。那个自称姓戚的管家每天会定时出现,汇报我的恢复情况,然后离开。
他不说自己是谁,也不说他的老板是谁,我也没问。直到我能下床走路那天,
他带来了一部新手机和一张新卡。手机里只有一个号码。「林**,老板说,
如果您准备好了,就可以打这个电话。」我拿着手机,走到落地窗前,看着外面蔚蓝的大海。
半个月的休养,身上的伤好了大半,可心里的那个窟窿,依旧灌着冷风。
我永远忘不了傅砚川的每一个眼神,宋知意的每一句嘲笑。这十年,他们偷走了我的人生。
我闭上眼,按下了拨号键。电话几乎是立刻就被接通了,
那头传来一个低沉又熟悉的男人声音,隔着电波,听不出情绪。「小晚。」我的眼泪,
在听到这个称呼的瞬间,掉了下来。那头的人似乎在等。我深吸一口气,擦掉眼泪,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齐叔……我爸妈十年前留给我的东西……现在还在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久到我以为他已经挂了。然后,
我听见他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林**,十年了。」他的声音里,终于带上了一丝情绪,
像是在心疼,又像是……在压抑着某种庞大的愤怒。7电话那头的男人,
是我父亲最信任的副手,齐峥。我父母意外离世后,我拒绝了他提出的一切帮助,
只想过一个最普通人的生活,自己打拼。我天真地以为,爱能战胜一切。
齐峥的声音打破了我的回忆:「林**,十年前,你父母将名下所有瑞宇资本的股权,
以信托形式交给我代管。协议的唯一条件是,在您满二十八岁之前,
我们不能主动干涉您的生活,除非……您亲自向我们求助。」我的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二十八岁。傅砚川偏偏选择在我二十七岁生日这天,举行这场将我彻底推入地狱的订婚宴。
原来不是巧合,是算计。他要在我拥有继承一切的资格前,彻底摧毁我的人格和意志。
「傅砚川在发了疯一样找你。」齐峥的声音听不出波澜,「他动用了所有人脉,
想在你彻底失控前,把你‘回收’,重新关起来。他现在大概还以为,
你是一只无家可归、只能依靠他存活的流浪猫。」我笑了。眼泪却不争气地滑落。
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那十年荒唐的自我感动,显得如此愚蠢,如此可笑。「齐叔。」
我开口,声音冷静得可怕,「我准备好了。」齐峥:「需要我为您做什么?」
「给我准备回沪市的机票。」我的目光投向窗外汹涌的潮水,「另外,帮我准备一份礼物。
一份……送给傅砚川和宋知意的大礼。」三天后,我回到沪市。迎接我的,
不再是郊区阴冷的别墅,而是一辆稳稳停在机场贵宾通道外的黑色宾利。齐峥为我拉开车门,
车内坐着四个瑞宇资本的顶级律师。「林**,这是您的身份证明文件,
以及董事会的委任状。」为首的律师递过来一个文件夹,「从今天起,
您是瑞宇资本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及执行董事长。」我接过那份沉甸甸的文件,
像接过了我迟到了十年的真正人生。齐峥递给我一个平板。「这是您要的礼物。」屏幕上,
是傅砚川这几日抓狂的所有监控录像。他砸了书房,将秦凯骂得狗血淋头,
给每一个可能认识我的朋友打电话,语气从最初的命令,到后来的烦躁,
